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陳春聲談“一流大學”(二)
更新:2023-09-16 19:32:20 高考升學網也就是說,我們還有32年的時間,要使中國的一些高校能通過高質量發展,達成這個目標。時不我待,這應該是雙一流建設的重要內涵之一,也是包括中山大學在內的一批中國最好大學的重要使命。
中國新聞周刊:你怎么定義“一流大學”?
陳春聲:我們學校領導班子對于一流大學的定義有共識,用通俗的話來說,首先,學生和家長在選擇就讀學校時,會首先想到這個大學;第二,國家有重大的戰略需求,或者碰到有急需解決的問題時,會首先想到這個大學;第三,國內、國際學術界的同行,需要討論和解決重大學術問題的時候,會首先想到這個大學的學者。
這三個“首先想到”,是羅俊校長提出來的,今年初寫進了學校黨代會的報告。我們認為,這樣的大學就可以稱為一流大學。
中國新聞周刊:你認為,放在世界的坐標軸內,中國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在哪里?
陳春聲:我覺得有兩個比較明顯的短板,一是教育教學層面,即人才培養的質量;二是管理架構和治理機制層面,還存在一些欠缺。
大學安身立命之本是培養人才,但中國的大學和國際上最好的大學在這個方面的差距還是相當大的,也是最不容易縮小的。
最簡單的,就以師生比來說,包括中山大學在內,中國大多數高等學校的生師比是18至20比1,國內最好大學的這個數字大概是13或14比1,而在歐美的許多一流大學,包括哈佛、牛津這樣的學校,他們的生師比是8或9比1。更直白地說,我們因為學生多、教師少,大學授課的方式與真正意義上的“小班教學”,還有很大一段距離。
而小班授課是教育界公認的、在高等教育領域提高學生培養質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即每個教學班控制在30人左右,一些專門的課程甚至是15人以下。在這樣的安排之下,老師才有可能個性化地關注學生的學業情況。
我們人才培養質量的聲譽還不夠好,這可以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。就是我們大學招收的國際學生,學業成績還不夠好,學術潛質也還不夠高。在國際上,一流大學的國際學生通常會占有較大的比例,而且,即使不能說國際學生的學業水通常會略高于本國學生的均水準,但起碼也不會比本國學生差。現在,我們絕大多數大學還做不到這一點。
我們會與國際學生開座談會,留學生們常常反映的一個問題是,自己的學業跟不上中國學生。用他們自己的話說,面對著通過高考才“拼殺”進入中山大學的中國同學,他們的感覺有點像“一只綿羊進入了狼群”。
作為教育者,我們自然有責任為這些自稱為“綿羊”的外國孩子提供更加適合他們的教育方式。但反過來想,為什么我們吸引來的大多是“綿羊”,而不是一大群“狼”?歸根結底,還是因為我們的人才培養質量不夠高,學術聲譽還不夠好,對“狼群”的吸引力不夠強。結果,為了所謂“國際化”的指標,就只能到境外圈一群乖乖的“綿羊”來培育。
在這個方面,年中山大學也進行了一些努力,提高國際學生的質量。我們建立了嚴格的國際學生入學考核程序,嚴格規定不準通過招生中介接收國際學生,同時適度增加國際學生招生數量,逐步提高學歷國際學生比例。
從2017年開始,我們每年面向東盟10國最好的若干所中學,經中學校長推薦,招收他們最好的畢業生,這是提高國際學生生源質量的一個有效嘗試,而且還服務于國家的“一帶一路”倡議。
另外一個短板是在學校的內部管理及運作機制方面,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比,還是有一定的差距。
中國大學的內部管理運作機制,基本都是和上級教育主管部門的機構設置對應。比如,教育部有研究生司、高教司、科技司、社科司、國際司,各個高校也就相應地設立研究生院、教務處、科技處、社科處和留學生處。但實際上,在世界一流大學里,留學生和本國學生的課程和教學安排,是不會分開管理的。我們的學生出國留學,一定是與所在國家的學生用同一個課程表的。
又如,本科生教學歸教務處管、研究生教學歸研究生院管,基本上也是中國大學獨有的制度安排。類似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。要實現進入世界一流大學前列的目標,這樣的架構問題還是比較大的。
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試點存在哪些問題?陳寶生回應2023-09-18 01:24:05
中外教育合作的方針是“請進來,走出去”2023-09-19 13:43:40
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優勢專業排名,2025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最好的專業排名2023-09-15 06:51:00
中山大學優勢專業排名,2025年中山大學最好的專業排名2023-09-18 15:53:03
2025年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大一新生軍訓安排和新生軍訓項目和時間2023-09-17 00:51:19
2025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大一新生軍訓安排和新生軍訓項目和時間2023-09-17 07:53:41
2025年中山大學大一新生軍訓安排和新生軍訓項目和時間2023-09-19 10:53:26
中山大學科學家團隊發現新的鼻咽癌易感基因2023-09-19 03:21:31
2025年中山大學優勢專業排名2023-09-18 01:55:05
2019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錄取分數線_歷年文科理科分數線2023-09-16 05:57:08
2019年中山大學錄取分數線及歷年文科理科錄取分數線2023-09-15 16:50:24
2019年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入學考試,入學指南,開學時間及新生轉專業2023-09-20 17:13:16
2019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入學考試,入學指南,開學時間及新生轉專業2023-09-20 23:34:13
2019年中山大學新華學院錄取分數線_歷年文科理科分數線2023-09-15 16:28:30
2019年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學費一年多少錢及生活費標準2023-09-19 00:51:47
2019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學費一年多少錢及生活費標準2023-09-18 06:21:04
2020年中山大學新華學院錄取通知書查詢,通知書什么時候發為什么還沒收到2023-09-14 14:57:04
2020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錄取通知書查詢,通知書什么時候發為什么還沒收到2023-09-15 00:06:37
2019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新生在哪個校區及新生開學報到時間2023-09-14 21:58:25
2019年中山大學入學考試,入學指南,開學時間及新生轉專業2023-09-18 15:35:18
2019年中山大學學費一年多少錢及生活費標準2023-09-19 01:57:12
2025年中山大學新生在哪個校區及新生開學報到時間2023-09-13 13:32:45
山西大同大學和安陽工學院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2025-05-23 18:32:04
河北高考排名在99400的物理類考生能報什么大學(原創)2025-05-23 18:30:39
四川高考排名在272050的理科類考生能報什么大學(原創)2025-05-23 18:29:19
湘潭大學和鄭州師范學院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2025-05-23 18:28:11
廣西民族大學和湖南文理學院芙蓉學院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2025-05-23 18:26:54
廈門理工學院在吉林高考專業招生計劃(人數+代碼)2025-05-23 18:25:42
鄭州工業應用技術學院在廣西高考專業招生計劃(人數+代碼)2025-05-23 18:24:09
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和遼寧師范大學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2025-05-23 18:23:01
天津中醫藥大學和山東建筑大學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2025-05-23 18:21:28
蚌埠學院和長江大學文理學院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2025-05-23 18:19:57
天津國土資源和房屋職業學院在浙江高考專業招生計劃(人數+代碼)2025-05-23 18:18:38
云南高考430分能上的公辦專科學校有哪些2025-05-23 18:17:05
上海市委宣傳部等領導來上海市繼光初級中學調研工作2023-09-16 20:56:31
教師專業成長的路上,我們結伴而行2023-09-21 02:54:25
最新圖文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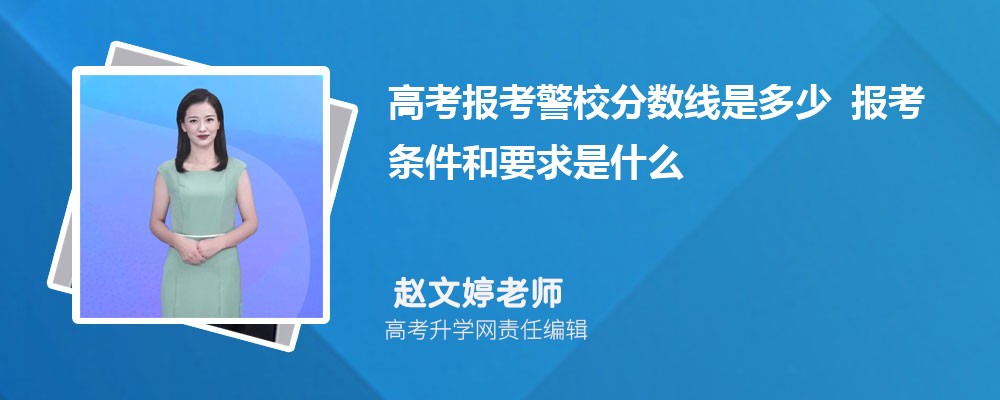
高考報考警校分數線是多少
時間:2024-09-19 08:0:34
2025年公布的全國高校第五
時間:2024-09-19 08:0:53
高考社會考生報考軍校的條件
時間:2024-08-12 09:0:45
社會考生報名高考的注意事
時間:2024-08-12 09:0:05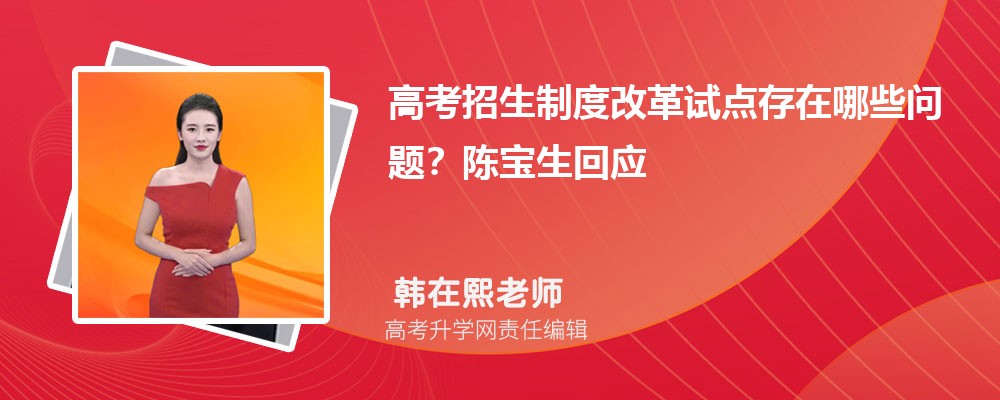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試點存在哪些問題?陳寶生回應
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試點存在哪些問題?陳寶生回應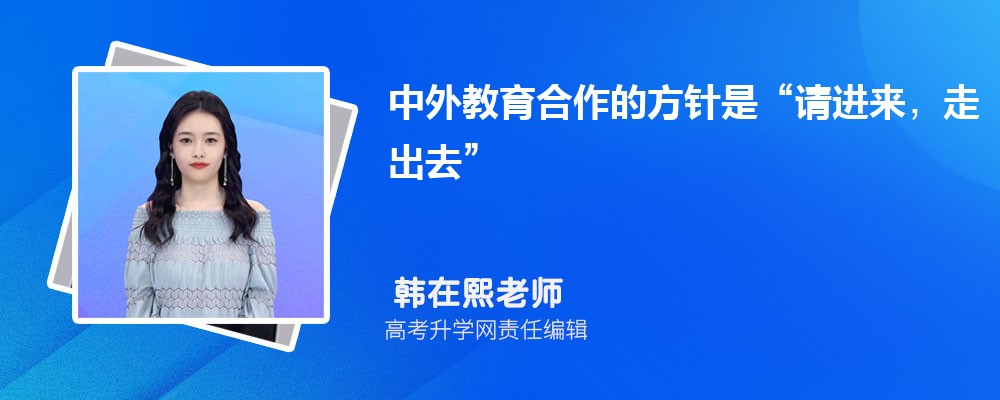 中外教育合作的方針是“請進來,走出去”
中外教育合作的方針是“請進來,走出去”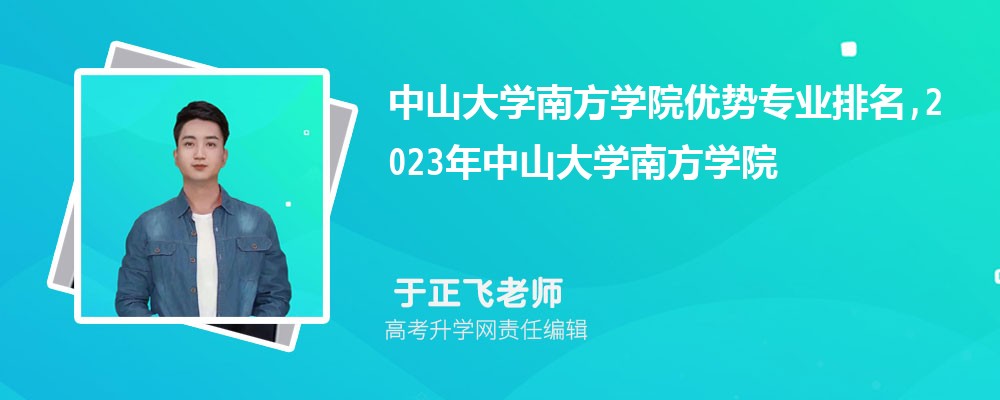 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優勢專業排名,2025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最好的專業排名
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優勢專業排名,2025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最好的專業排名 中山大學優勢專業排名,2025年中山大學最好的專業排名
中山大學優勢專業排名,2025年中山大學最好的專業排名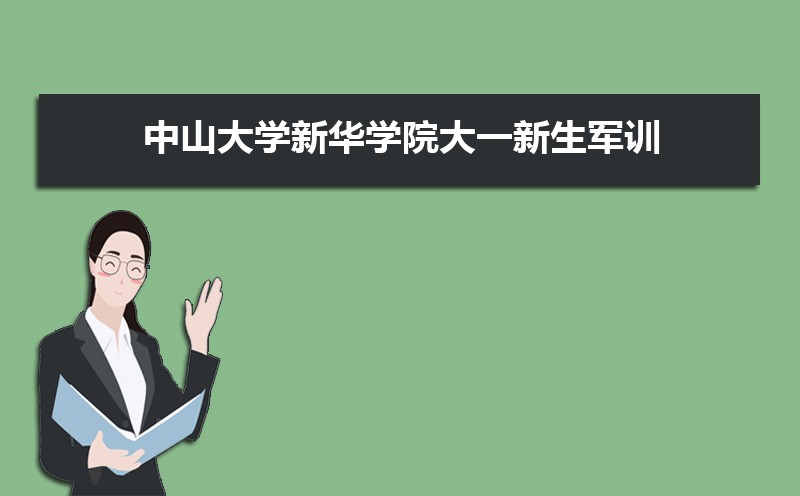 2025年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大一新生軍訓安排和新生軍訓項目和時間
2025年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大一新生軍訓安排和新生軍訓項目和時間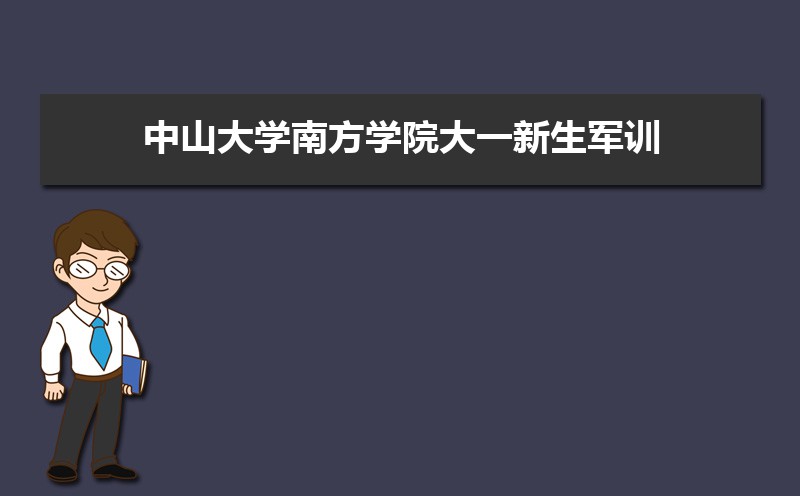 2025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大一新生軍訓安排和新生軍訓項目和時間
2025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大一新生軍訓安排和新生軍訓項目和時間 2025年中山大學大一新生軍訓安排和新生軍訓項目和時間
2025年中山大學大一新生軍訓安排和新生軍訓項目和時間 中山大學科學家團隊發現新的鼻咽癌易感基因
中山大學科學家團隊發現新的鼻咽癌易感基因 2025年中山大學優勢專業排名
2025年中山大學優勢專業排名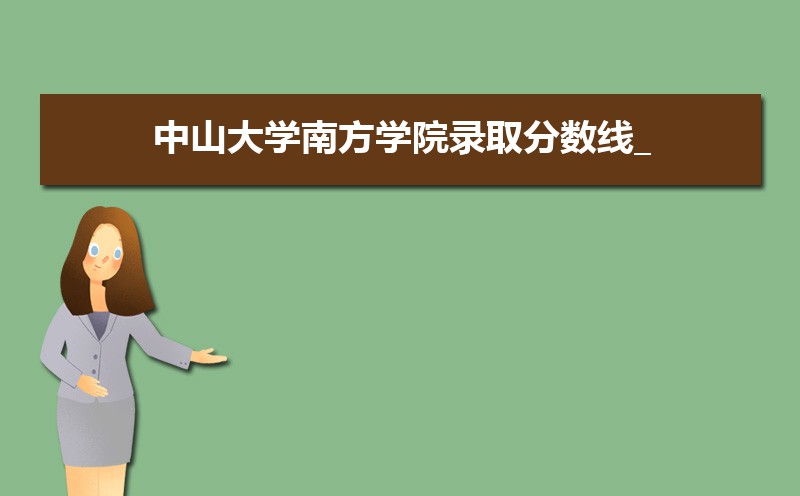 2019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錄取分數線_歷年文科理科分數線
2019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錄取分數線_歷年文科理科分數線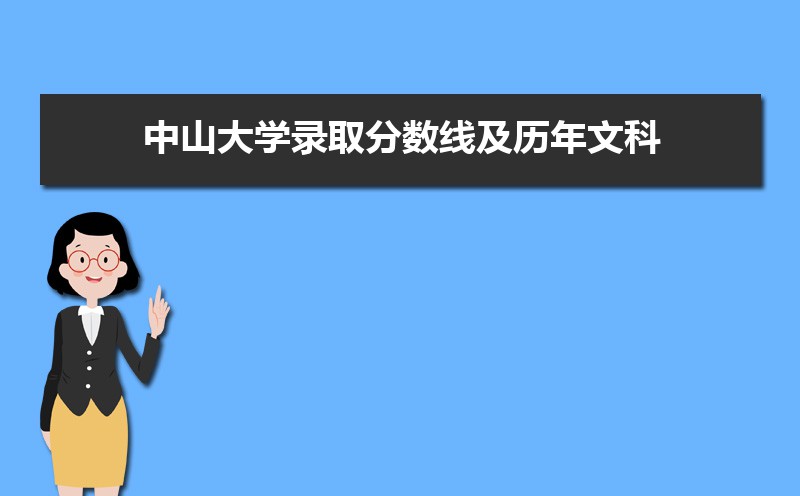 2019年中山大學錄取分數線及歷年文科理科錄取分數線
2019年中山大學錄取分數線及歷年文科理科錄取分數線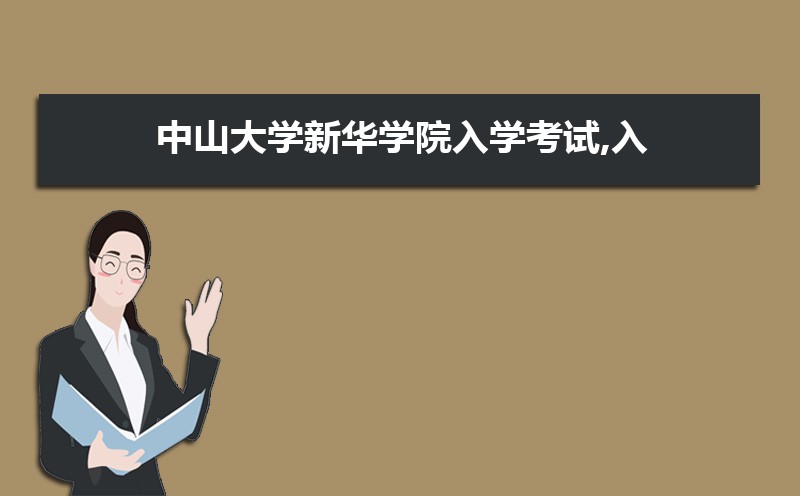 2019年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入學考試,入學指南,開學時間及新生轉專業
2019年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入學考試,入學指南,開學時間及新生轉專業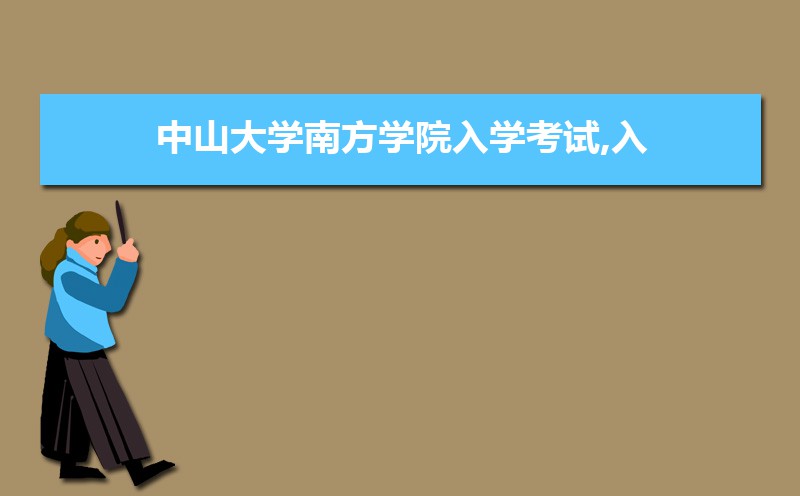 2019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入學考試,入學指南,開學時間及新生轉專業
2019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入學考試,入學指南,開學時間及新生轉專業 2019年中山大學新華學院錄取分數線_歷年文科理科分數線
2019年中山大學新華學院錄取分數線_歷年文科理科分數線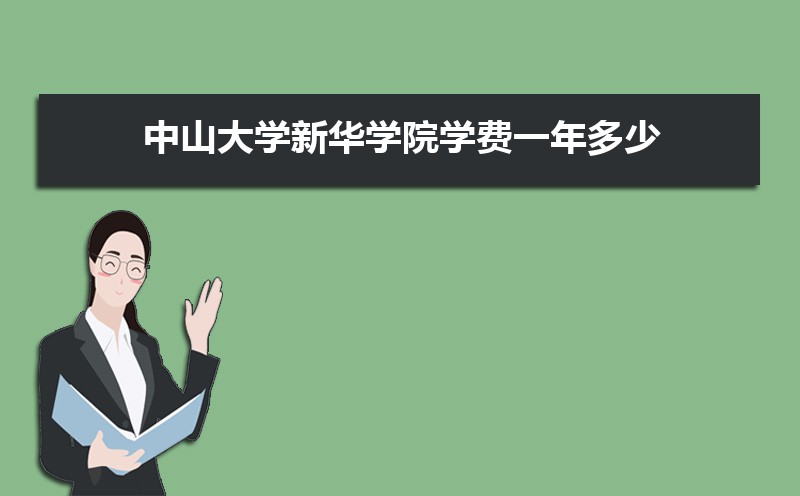 2019年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學費一年多少錢及生活費標準
2019年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學費一年多少錢及生活費標準 2019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學費一年多少錢及生活費標準
2019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學費一年多少錢及生活費標準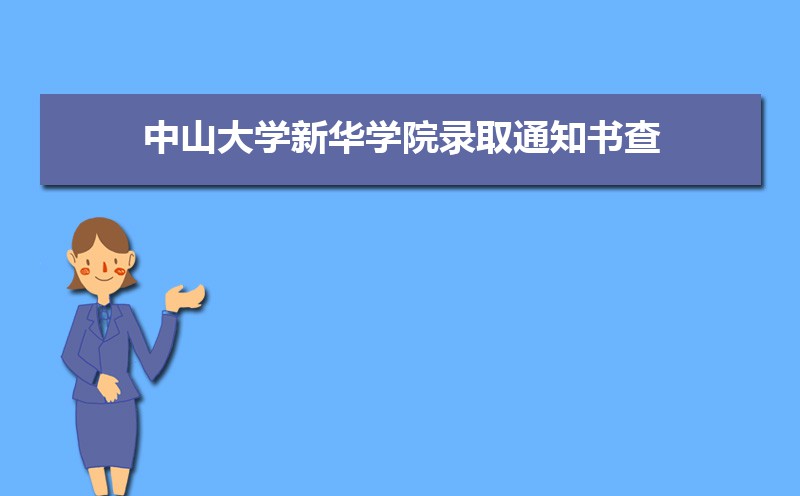 2020年中山大學新華學院錄取通知書查詢,通知書什么時候發為什么還沒收到
2020年中山大學新華學院錄取通知書查詢,通知書什么時候發為什么還沒收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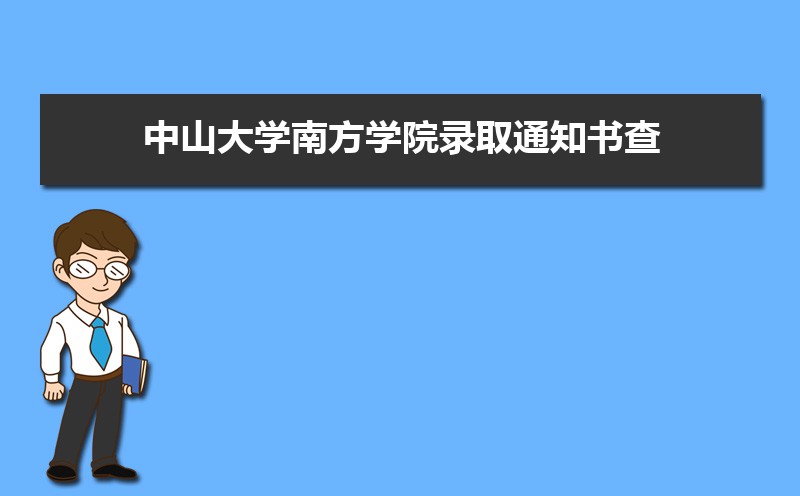 2020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錄取通知書查詢,通知書什么時候發為什么還沒收到
2020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錄取通知書查詢,通知書什么時候發為什么還沒收到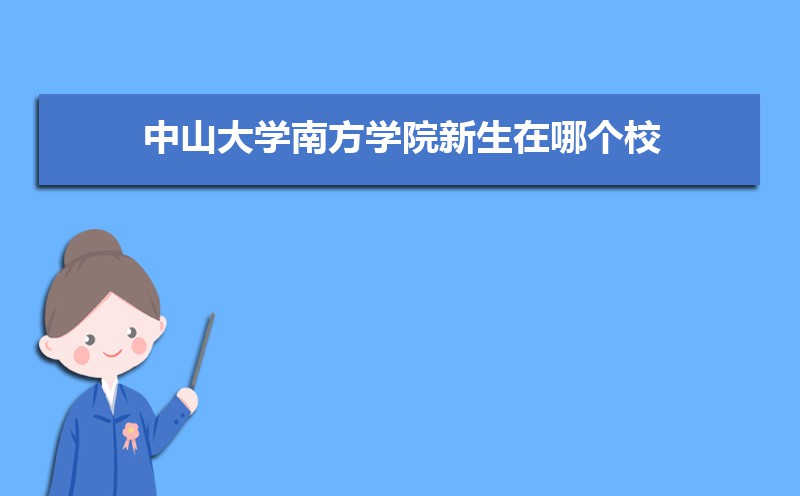 2019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新生在哪個校區及新生開學報到時間
2019年中山大學南方學院新生在哪個校區及新生開學報到時間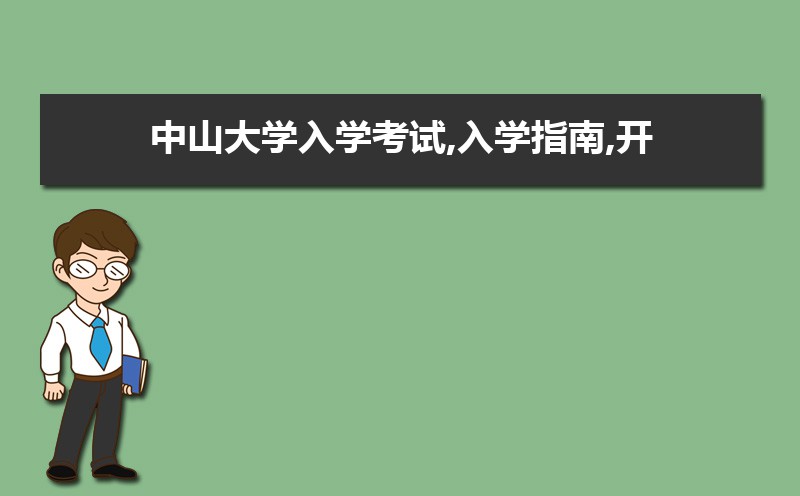 2019年中山大學入學考試,入學指南,開學時間及新生轉專業
2019年中山大學入學考試,入學指南,開學時間及新生轉專業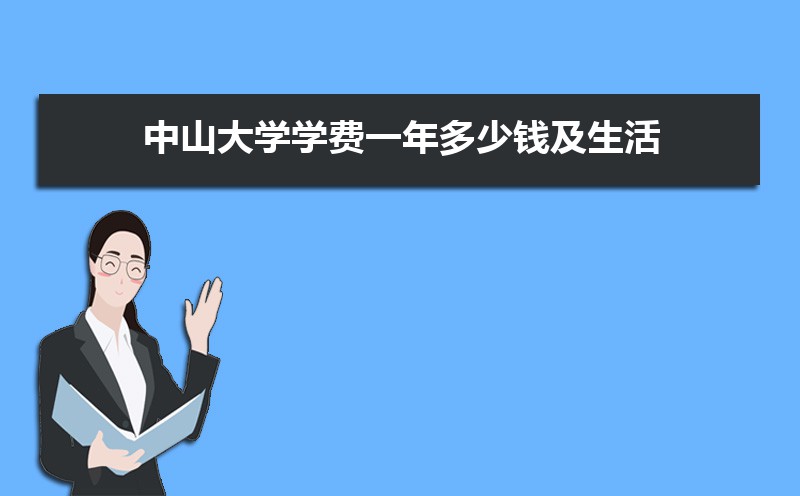 2019年中山大學學費一年多少錢及生活費標準
2019年中山大學學費一年多少錢及生活費標準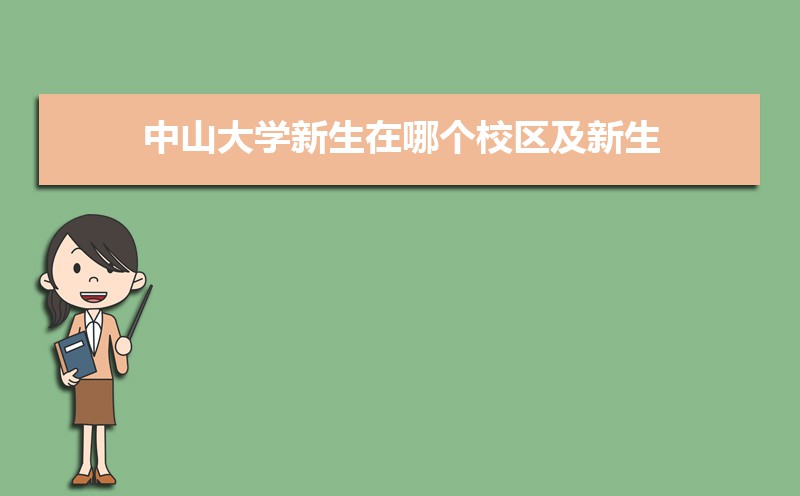 2025年中山大學新生在哪個校區及新生開學報到時間
2025年中山大學新生在哪個校區及新生開學報到時間 山西大同大學和安陽工學院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
山西大同大學和安陽工學院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 河北高考排名在99400的物理類考生能報什么大學(原創)
河北高考排名在99400的物理類考生能報什么大學(原創) 四川高考排名在272050的理科類考生能報什么大學(原創)
四川高考排名在272050的理科類考生能報什么大學(原創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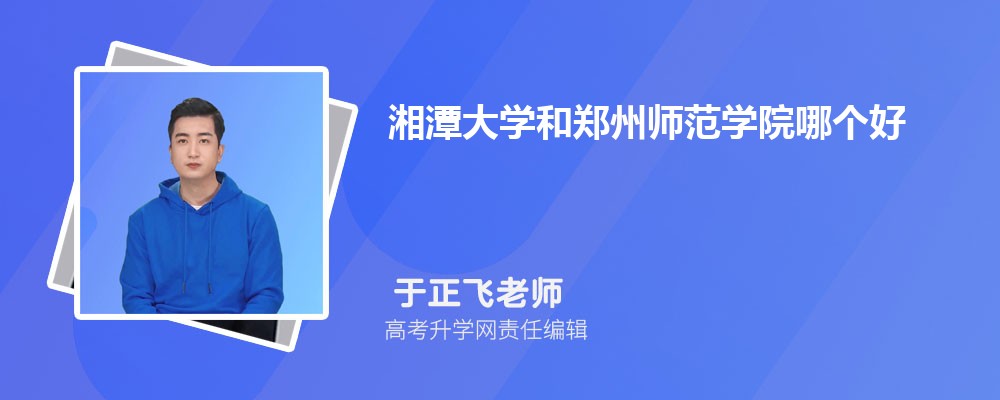 湘潭大學和鄭州師范學院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
湘潭大學和鄭州師范學院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 廣西民族大學和湖南文理學院芙蓉學院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
廣西民族大學和湖南文理學院芙蓉學院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 廈門理工學院在吉林高考專業招生計劃(人數+代碼)
廈門理工學院在吉林高考專業招生計劃(人數+代碼) 鄭州工業應用技術學院在廣西高考專業招生計劃(人數+代碼)
鄭州工業應用技術學院在廣西高考專業招生計劃(人數+代碼)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和遼寧師范大學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
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和遼寧師范大學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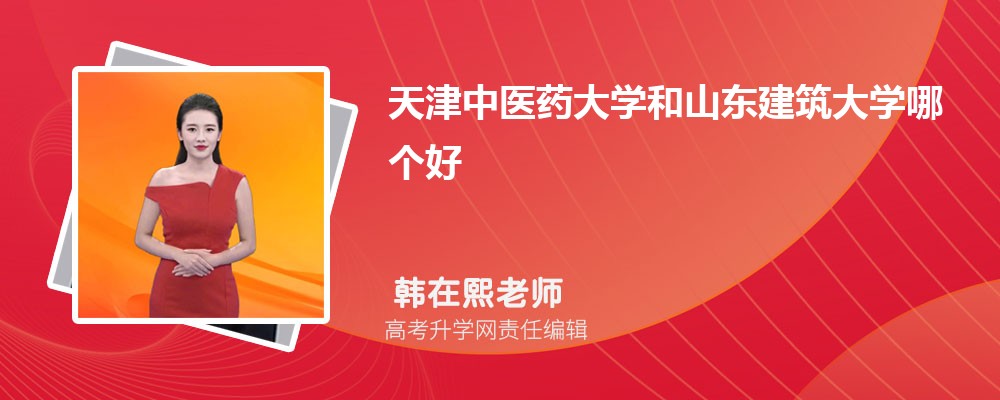 天津中醫藥大學和山東建筑大學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
天津中醫藥大學和山東建筑大學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 蚌埠學院和長江大學文理學院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
蚌埠學院和長江大學文理學院哪個好 分數線排名對比 天津國土資源和房屋職業學院在浙江高考專業招生計劃(人數+代碼)
天津國土資源和房屋職業學院在浙江高考專業招生計劃(人數+代碼) 云南高考430分能上的公辦專科學校有哪些
云南高考430分能上的公辦專科學校有哪些 上海市委宣傳部等領導來上海市繼光初級中學調研工作
上海市委宣傳部等領導來上海市繼光初級中學調研工作 教師專業成長的路上,我們結伴而行
教師專業成長的路上,我們結伴而行